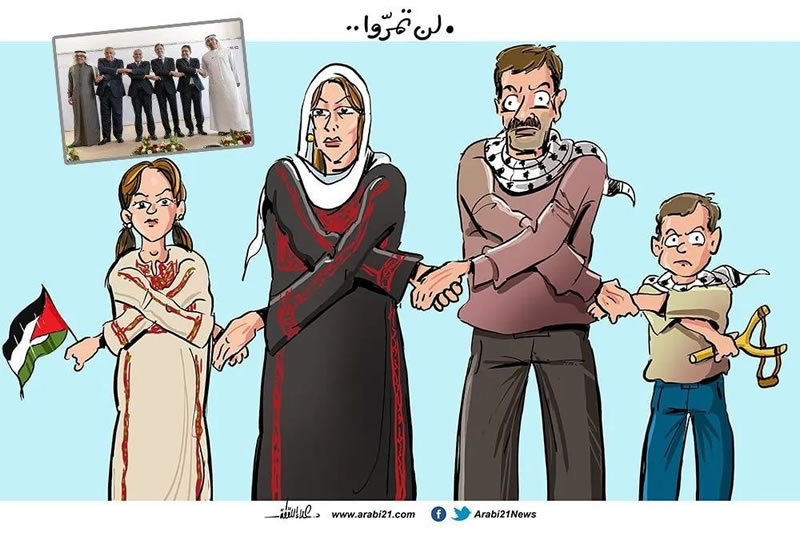本文作者:拉姆齊•巴魯德(Ramzy Baroud)是一名巴勒斯坦記者,同時擔任《巴勒斯坦紀事報》(The Palestine Chronicle)的主編。
在過去的十四個月裡,我收到了來自加沙的家人們發來的數百條資訊。這些資訊有時急迫、充滿驚恐,有時則平靜,仿佛在逆境中尋找到了一種安然的歸屬感。
發來這些消息的人中,有些已經在以色列的襲擊中遇難,比如我的姐姐,索瑪•巴魯德博士;還有一些人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兄弟姐妹、親友和鄰居。
然而,令人震撼的是,無論這些資訊多麼令人心碎,他們從未質疑過自己的信仰。他們幾乎每次都以真誠的問候開篇,關心我的近況,問候我的孩子們。
以下是一些信件的節選,我做了必要的刪減和調整,以便更清晰地傳達他們的聲音。
易卜拉欣的信
你怎麼樣?我們都還好,只是被迫離開了沙提難民營。昨天,以色列軍隊進駐了難民營。我們整條街都被摧毀了,我們的家也沒了。 الحمد لله——讚美真主。
索瑪的信
你好嗎?孩子們怎麼樣?這樣的時刻讓我明白,所有的物質財富都不重要。唯有家人和同胞的愛,才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
我們被迫逃離了卡拉拉,男孩們去了更南邊的地方,而我帶著女兒和外孫到了代爾巴拉赫。我不知道H(她的丈夫)怎麼樣了。軍隊的推土機開始拆毀我們的街區時,我們還在家裡。我們連夜逃了出來。
艾莎的信
E(她的丈夫)在以色列入侵的第一天就被殺了。A(她的兒子)在聽到父親犧牲的消息後消失了。他說要為父親復仇。我很害怕,不知道該怎麼辦。”
薩爾娃的信
堂兄,艾莎的兒子A犧牲了。他才19歲,在賈巴厘亞的戰鬥中陣亡。艾莎現在帶著倖存的孩子在拉法的某個地方。他們的嬰兒患有先天性心臟病。你知道有沒有什麼慈善機構可以幫助她?她們住在一個帳篷裡,沒有食物,也沒有水。
易卜拉欣的信
我們逃到了謝法醫院。後來,以色列軍隊也攻進了醫院。他們把所有的男人帶到外面,讓我們排成一列。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放過了我。其他人都沒有這麼幸運——所有的男人都被處決了。納賽爾的兒子(我的侄子)就在我面前被殺。他們當場開槍。我們至今仍被困在醫院裡。
索瑪的信
哥哥,我的丈夫被殺了。我那可憐的夫君,本就身體不好,沒法及時逃跑。有人說他被無人機擊中了頭部。但當我們回到事發地點,卻找不到他的遺體。現場是一片廢墟和垃圾堆。我們日夜不停地挖掘,卻一無所獲。我只想為他舉行一個體面的葬禮。
艾莎的信
薩爾娃有跟你說過慈善機構的事嗎?我真的很需要幫助。我的孩子快不行了。我給她取名瓦法,是為了紀念她的姨媽(瓦法26歲,在戰爭的前幾周被炸死,和她5歲的兒子紮伊德以及丈夫穆罕默德一起遇難)。她幾乎喘不過氣來,聽說有人可以通過拉法口岸離開加沙,有些重傷者和病人被送往阿聯酋。請幫幫我。
瓦利德的信
你聽到停火的消息了嗎?我們又逃回了加沙市中心,因為南部已經不安全了。他們(以色列軍隊)告訴我們去“安全區”,可後來,他們又轟炸了那些帳篷裡的避難者。我親眼看到鄰居被活活燒死。我已經太老了(他75歲了)。請告訴我,戰爭快結束了吧?
易卜拉欣的信
堂兄,你好嗎?我想告訴你,納賽爾(我的兄弟)被殺了。他是在紮伊通排隊領麵包時遇害的。在他的兒子們殉難後,他成了孫輩們唯一的依靠。他帶著孩子們去領救濟物資,結果,以色列軍隊炸了等待的人群。他的胳膊被炸斷,最後因失血過多而死。
索瑪的信
我在努賽拉特的時候,那裡發生了大屠殺。那一天,278人遇難,800多人受傷。我走過那片區域時,完全不知道那裡剛剛經歷了一場血腥的屠殺。我只是想回卡拉拉,看看我的孩子們。到處都是屍體,橫七豎八地躺在街頭。大多數已經被嚴重毀壞,有些還在呻吟,拼命抓住生命的最後一絲希望。我想幫忙,但卻無能為力。我從一具屍體走到另一具屍體,握住他們的手,凝視著那些臨死前的眼神。
我曾在急診室工作多年,但在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無助。我覺得自己也在那天死去了。
(我的姐姐索瑪醫生于10月9日遇難。當時,她剛離開醫院去看望自己的孩子,途中被以色列空襲擊中。)
易卜拉欣的信
堂兄,請接受我對你姐姐殉難的哀悼。她永遠是我們家族的驕傲。
艾莎的信
瓦法今天早上去世了,在穆薩維的帳篷裡。沒有藥品,沒有食物,也沒有牛奶。唯一讓我感到一絲慰藉的,是她已經回歸了真主的樂園。
瓦利德的信
堂兄,你好嗎?我們還好。我們失去了所有,但感贊真主,我們仍在堅持。你知道戰爭什麼時候結束嗎?也許再過一周,或者兩周?我真的太老了,太累了。
這是一段無盡的苦難,卻也是一段關於信仰、希望與堅韌的故事。
每一句“感贊真主”的背後,都是他們對生存的渴望、對信仰的堅定,以及對美好未來的無盡祈願。
-------------
編輯:葉哈雅
出處:IslamCity
原文:Letters from Gaza – ‘Alhamdulillah. We Are Not Okay’
連結:https://tinyurl.com/27rk2p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