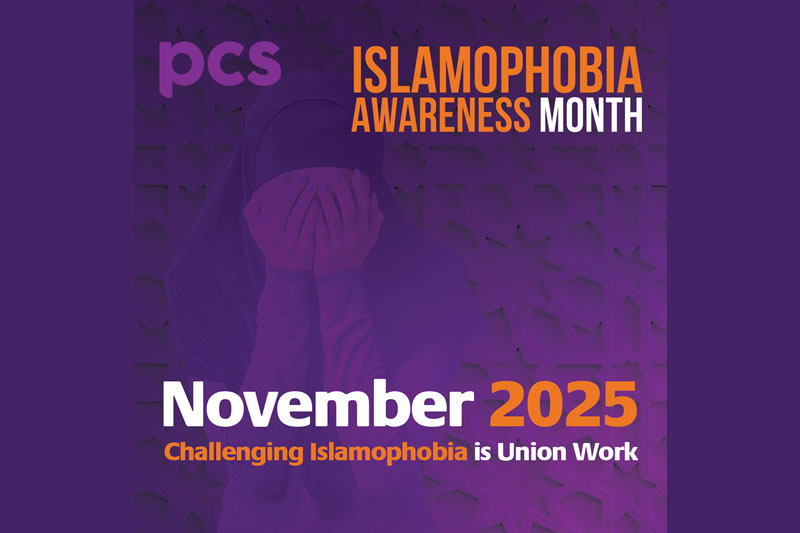隨著針對穆斯林的暴力頻頻出現在公共視野,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多數派政治將仇恨轉化為娛樂,而大眾的沉默,則成了最便捷的共謀。
當今的印度,每個清晨都從兩條平行的新聞線開始。其中一條出現在電視螢幕上,經過精心編排:內容圍繞貶低巴基斯坦、宣揚印度教的自豪感,以及那場關於“新印度”的無休止政治戲劇。另一條,則是更貼近現實卻從來都不會被播出,那就是印度穆斯林每天遭遇的暴力、騷擾、拘捕與汙名化的生活日常。在這兩種新聞之間所傳遞出的資訊,總是令人不寒而慄:印度穆斯林的苦難要麼被抹去,要麼被當作一場表演,被多數民眾像觀看娛樂節目那樣消費;而印度穆斯林自身卻被迫活得像是永遠的罪犯——不斷被指控,卻從未有人傾聽。
以今年九月在印度北方邦阿紮姆加爾(Azamgarh)發生的一起事件為例:一名七歲的穆斯林男孩被殘忍殺害,他的遺體被人塞進袋子中,他的印度教鄰居發現遺體時表現出令人心寒的冷漠,這些鄰居後來全被逮捕。這則消息在地方媒體上短暫出現,但很快從電視新聞中消失,被那些鼓吹穆斯林對立情緒的“愛情聖戰”論、邊境緊張局勢或印巴板球賽的激烈辯論所取代。一個穆斯林孩子的死亡,不符合“舉國憤怒”的敘事劇本,它只是悄然進入了那份已經“暴力正常化”的無聲檔案。社會學家斯坦利·科恩曾提出“否認狀態”這一概念,即:某些社會的暴行並非被掩蓋,而是被如此習慣性地吸收,以至於人們不再對此類暴行感到震驚。而這,正是今日印度的現狀:穆斯林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殘忍殺害,而多數人卻把它當作生活中的娛樂新聞和背景雜音。
與此同時,仇恨不僅體現為沉默,也成了一種“娛樂表演”。當印度北方邦的坎普爾(Kanpur)穆斯林舉著寫有“我愛穆罕默德”的標語時,印度警方的反應不是保護,而是針對1300多名當地穆斯林的立案,並展開大規模逮捕。連表達愛的舉動,都被定為罪行,然而,當一些印度教極端團體在馬哈拉斯特拉邦(Maharashtra)或中央邦(Madhya Pradesh)集會,並高喊公開的民族仇恨、煽動性口號時,媒體的鏡頭要麼刻意美化,要麼乾脆轉移視線。換言之,在印度,針對穆斯林的暴力已經演變成一種舞臺劇,在這場戲裡,穆斯林永遠是被審判的角色,而極端印度教民族主義勢力則被包裝成“文明的守護者”。
這種“選擇性可見”並非偶然,而是刻意為之。在印度中部重要城市印多爾(Indore)興起的所謂“無聖戰市場”運動中,一夜之間,所有穆斯林商販被驅逐,這是一種經濟層面的私刑式排斥。無數穆斯林家庭失去生計,孩子被迫輟學,他們甚至被迫向鄰居乞討食物。然而,印度的官方媒體卻將此事包裝為“治安調整”,對於這種所謂“整頓運動”背後的人道危機與代價,卻是隻字不提。一些印度教極端民族主義團體甚至在社交媒體上大肆慶祝,把針對穆斯林的壓迫與剝奪當成一種網路娛樂。原本應成為全國醜聞的事件,被輕描淡寫地呈現為日常的“地方糾紛”。
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長約吉·阿迪蒂亞納特(Yogi Adityanath)正是這種“表演文化”的化身。阿迪蒂亞納特常在官方講臺大肆發表針對穆斯林的激烈言論,稱穆斯林為印度社會的“滲透者”,是“恐怖分子的同情者”。可怕的是,這些聲音並非個例,也並非來自邊緣群體,而是出自掌權的精英階層。然而,對於執政黨的反穆斯林情緒,所謂的反對黨並沒有憤怒反駁,而是以“溫和版”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來回應,競相展示誰更能顯得“親印度教”,穆斯林的恐懼與悲慘則被徹底壓制。這種跨黨派的默契已經表明:在當今印度,穆斯林不再被視為獨立的政治主體,而只是政治舞臺上的道具。
造成這種局面的終極代價,不僅體現在身體層面,更體現在心理與存在意義上的雙重創傷。今天,作為穆斯林生活在印度,就意味著被永久懷疑——在清真寺裡被注視,在市場中被評判,在課堂上被質疑。每一次星期五的聚禮都像是一場冒險,每一次從擴音器傳出的祈禱聲,對一些人而言都成了挑釁,儘管那聲音只不過是一個群體最本真的精神脈搏。烏爾都詩人薩希爾·盧迪安維曾寫道:“那些以印度教為傲的人,如今身在何處?”這個問題在今天依舊回蕩:如果這就是所謂的印度之偉大,為什麼它每天都需要以羞辱穆斯林為證?
出生于烏干達的穆斯林學者馬哈茂德·曼達尼(Mahmood Mamdani)提供了一個理解當下現象的分析框架。在他那本著名的《好穆斯林,壞穆斯林:美國、冷戰與現代性政治》(Good Muslim, Bad Muslim: America, the Cold War, and the Roots of Terror)一書中,他解釋了國家和社會如何將穆斯林分成兩類:一種是“被接受的”穆斯林——安靜順從、不引人注目;另一種則是“危險的”穆斯林——敢於抗爭不公、敢於維護尊嚴。在印度,這種劃分被日復一日地武器化,如果一個穆斯林隱藏信仰、刻意保持隱形,他就可以被容忍;但如果一個穆斯林公開表達身份,或者在公開“我愛穆罕默德”、要求平等權利、拒絕被抹黑,卻會立刻被視作“罪犯”。曼達尼提醒我們,這並非宗教學問題,而是權力問題:誰有權定義何為“合法”,又有誰必須永遠活在懷疑的陰影之下。
正因如此,一些針對穆斯林的私刑視頻會像表情包一樣在社交軟體上廣為流傳,某些電視主持人在散播“穆斯林人口陰謀論”時會露出冷笑,極端印度教暴徒在焚毀穆斯林店鋪後依舊放聲大笑……仇恨早已不僅僅是政治,它成了一種集體性的娛樂。當殘忍與暴行被演繹成喜劇,當羞辱被包裝成黃金時段的節目腳本時,民主與極權之間的界限早已徹底崩塌。
歷史早已警示我們:那些把少數群體的痛苦當作娛樂的社會,最終都無法逃脫腐敗與崩壞。在納粹集會上保持沉默的德國自由派,在黑人私刑事件中冷漠旁觀的美國人,以及在加沙轟炸期間歡呼的人們。這一切都提醒我們:以仇恨為娛樂所建立的社會,終將被這種仇恨吞噬。
因此,就讓我們再次回到那個最初的問題:我們究竟是穆斯林,還是“罪人”?這個問題不僅僅需要穆斯林來回答,它更是印度多數人必須面對的抉擇:他們是否要繼續把仇恨當作娛樂電視觀看,還是願意關掉那塊充滿恥辱的螢幕?
因為,當有一天仇恨成為全國唯一的娛樂形式時,片尾字幕所掠過的不僅是穆斯林的屍體,而是整個共和國的死亡。到那時,歷史不會追問你是印度教徒還是穆斯林,也不會問你是右翼還是自由派,它只會問一個問題——為什麼一個以文明而自豪的現代社會,會把殘忍變成喜劇,會把沉默當作允許?擺在印度多數人面前的問題,已不再是寬容或世俗主義,而是他們是否還能認出鄰人身上的人性。
如果今天的你在穆斯林被當作“罪人”受罰時鼓掌叫好,那麼,當你明天醒來時,你或許會發現,那個你曾為之歡呼的國家,已經變成了你的牢籠。到那時,仇恨的笑聲將是這個世界唯一殘存的聲音。
--------------
編輯:葉哈雅
出處:Aljazeera
原文:Are We Muslims or Mujrims? How hate became India’s daily entertainment
連結:https://tinyurl.com/26shsp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