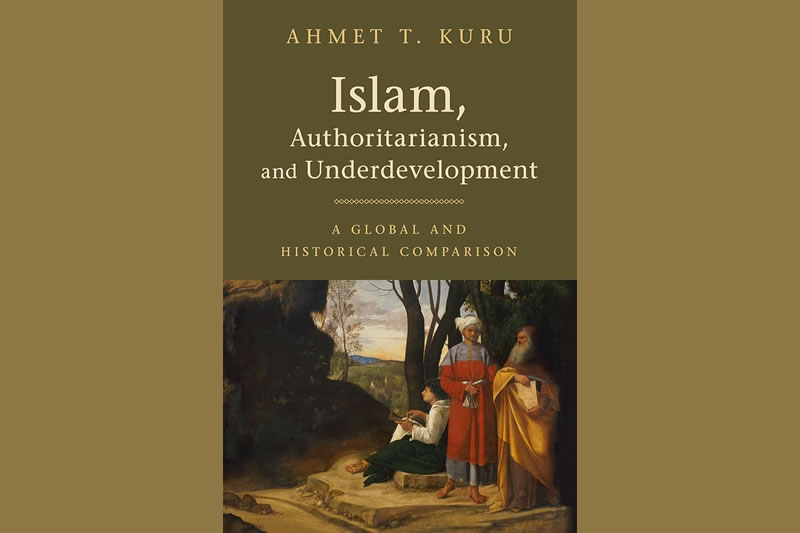自“9·11”事件以來,穆斯林世界一直處於全球輿論和學界的聚光燈下。暴力、威權與發展停滯的問題頻頻引發關注,僅在2009年,全球三分之二的戰爭和三分之一的軍事衝突,就發生在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
根據美國智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發佈於2013年的資料,在全球49個穆斯林國家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政權被歸類為民主國家,而在全球195個國家中,被劃為民主國家的比例則為五分之三。穆斯林國家在人均國民總收入、識字率、受教育年限和平均壽命等經濟與社會發展指標上,普遍表現不佳。
這種貌似客觀實則及其片面的調查,歸根結底就是試圖解釋穆斯林世界與暴力、威權主義與欠發達關聯起來。通常來說,西方社會慣用三種理論來試圖解釋穆斯林與這三者的關係。第一種是“本質主義”理論,認為一切問題的根源就在於伊斯蘭經典或歷史中某些“固有”的特徵,西方和部分穆斯林社會中的伊斯蘭批評者都持有這種觀點;第二種是“後殖民、反殖民”理論,認為西方殖民勢力對穆斯林國家資源的長期掠奪是關鍵原因。這種理論更注重國際因素,在許多伊斯蘭主義者和世俗主義思想群體中都很受歡迎,因為他們共同持有反西方立場;第三種是“制度主義”理論,主張穆斯林國家欠發達的原因在於缺乏有效的制度。
土耳其裔政治學家、聖達戈州立大學教授艾哈邁德·T·庫魯(Ahmet T. Kuru)則對上述三種理論都提出了質疑,在其研究翔實、發人深省的著作《伊斯蘭、威權主義與欠發達:全球與歷史的比較》,庫魯教授提出了一種全新的解釋。
庫魯教授通過詳述西元8至12世紀穆斯林社會在哲學和經濟上的輝煌成就,即回溯伊斯蘭文明的黃金時代,否定了“本質主義”的觀點,從而證明伊斯蘭與進步科學並不矛盾。他也不同意反殖民主義者的解釋,因為他指出穆斯林社會在18世紀中葉,即西方殖民到來之前,就已陷入嚴重的衰落和社會政治危機。至於制度主義,他認為制度是人類創造的,因此需要進一步探究:早期伊斯蘭歷史中,哪些群體或階層建立了強大的制度,而在後來的歷史中又是誰未能做到這一點。
庫魯教授重點論述了宗教、政治、知識和經濟階層之間的互動關係。他認為,不論是在穆斯林世界還是在歐洲或整個西方世界,社會在思想與經濟層面的成敗,幾乎都取決於這些階層關係。庫魯教授全書的核心論點是很簡單,即:早期穆斯林的偉大成就,得益于知識份子與資產階級商人階層的領導作用。
然而,自11世紀起,穆斯林世界的階層關係發生巨大轉變,最終導致停滯與衰落,“烏里瑪—國家聯盟”,即宗教學者(烏里瑪)與王權統治者結成合作關係,學者通過國家資助的宗教學校為政權提供合法性與宗教背書,政權則給予他們地位、資源和影響力。這種聯盟強化了正統宗教與王權,但也邊緣化了獨立思想家與商人階層,擠壓了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的空間,長期抑制了學術創新與經濟活力,對伊斯蘭文明的停滯和衰落產生了深遠影響。
換言之,這位土耳其裔學者將穆斯林世界的停滯追溯到烏里瑪—國家聯盟的主導地位。
在伊斯蘭早期,思想家和商人引領社會發展,而彼時的歐洲仍在宗教正統與軍權統治下掙扎。11世紀,軍事實體與烏里瑪宗教學者之間結成關鍵性的聯盟,改變了此後的歷史走向。這一聯盟一直延續至今,它邊緣化了知識份子與商人,扼殺了競爭與創造力。
庫魯強調,烏里瑪—國家聯盟,或者所謂的“政教合一”體制,既不是古蘭經和聖訓中的必然要求,也不是伊斯蘭早期歷史中的固定模式。事實上,在早期伊斯蘭歷史中不乏政教分離的例子,他進一步指出,宗教與政治結合的觀念,實為前伊斯蘭時代波斯薩珊王朝的思想,後期則被錯誤地套用在伊斯蘭之上。
在西元8至12世紀,穆斯林世界湧現出一大批卓越的博學者,他們在醫學、數學、天文學、哲學、製圖學、農業等領域貢獻卓著,締造了震驚全世界的伊斯蘭文明黃金時代,同期的穆斯林商人也被認為發明了多種銀行工具,如支票和匯票。
在伊斯蘭早期,穆斯林學者們刻意保持與政治權力的距離,他們認為接近權力中心必然導致腐敗,而是依靠商業資助,從而與商人形成緊密聯繫。許多宗教學者和思想家本身就是商人,或由商人資助。一項研究顯示,在西元8世紀至11世紀中期的近四千名伊斯蘭學者中,僅有9%由國家供養,其餘91%都依靠商業和中產階級支持。
正因遠離政治權力,早期的穆斯林學者與思想家才能享有相對自由的思想空間,他們對王權統治者大多感到失望和疏離。倭馬亞王朝因迫害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的後裔、依靠暴力鞏固統治而被廣泛認為缺乏宗教合法性,這種與國家保持距離的態度,延續到了取而代之的早期阿拔斯王朝時期。
在這一時期,四位獨立的著名宗教學者,阿布·哈尼法、馬立克、罕百里與沙斐儀,創立了遜尼派的四大教法學派,同時拒絕屈服于國家權力與王權,他們每個人都曾因持不同意見而遭到當局監禁和迫害。
西元11世紀,遜尼派穆斯林世界發生了關鍵性轉折,烏里瑪與軍事實體之間形成了宗教與國家的聯盟,即所謂的“政教合一”伊斯蘭國家。由此,宗教學者通過國家主導的宗教學校逐漸淪為國家的僕從,經濟逐漸通過“伊克塔”土地分封與稅收承包制度被軍事化,而思想家、哲學家、非政府學者與商人階層則被邊緣化。
這一轉變發生在阿拔斯王朝哈里發時期,其背景是來自競爭性的什葉派王朝,即埃及的法蒂瑪王朝、巴格達的布韋王朝,以及伊拉克的莫爾太齊賴派的挑戰。塞爾柱帝國宰相尼紮姆·穆勒克戰略性地設立了尼紮米亞宗教學校,進一步穩固了烏里瑪—國家聯盟在整個穆斯林世界的地位。像伊瑪目·安薩里這樣的學者,通過猛烈抨擊什葉派與莫爾太齊賴派,進一步鞏固了遜尼派的正統性。與此同時,商人階層被削弱,而軍事階層則憑藉土地收入分配獲得經濟主導地位。
來自歐洲的十字軍東征以及來自亞洲的蒙古入侵,進一步推動了烏里瑪—國家聯盟的壯大。面對外部威脅,穆斯林社會把希望寄託于軍事英雄和宗教精英身上,進一步忽視了普通學者、思想家和商人。最終,塞爾柱的烏里瑪—國家聯盟模式被阿尤布馬穆魯克、奧斯曼、薩法維以及莫臥兒帝國所效仿。
庫魯教授還指出,儘管奧斯曼、薩法維和莫臥兒帝國在16世紀之前一度實現了經濟增長,但宗教學校體系與烏里瑪—國家聯盟卻壓制了創造力,並邊緣化了獨立的學者與商人。本書在涉及伊朗和印度的部分相對薄弱:在伊朗,庫魯未能解釋“商人—什葉派烏里瑪聯盟”(而非烏里瑪—國家聯盟)如何在反對國家王權中發揮強大作用,這一作用最終導致了1906年與1979年革命。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前,伊朗什葉派烏里瑪的經費主要來源於民眾的私人捐款(胡姆斯)。在莫臥兒印度,除了保守的奧朗則布時期外,穆斯林宗教學者與莫臥兒帝國君主之間大多處於對立關係,尤其是在阿克巴和賈漢吉爾時期。
若要理解穆斯林世界所面臨的暴力於衝突問題,就必須試著理解穆斯林社會中的歷史性威權主義。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大多數穆斯林國家,無論是由世俗派還是伊斯蘭主義領導人統治,依舊保持威權模式,推行壓迫性政策,導致戰爭、內亂和衝突。大多數世俗領導人出身軍隊,因此忽視了知識份子和商人的作用。
威權統治者往往依賴與烏里瑪的聯盟以及石油租金來維持政權。當今世界28個“租金國家”中有22個是穆斯林國家,這些國家超過40%的收入依賴石油。與傳統的土地租金不同,當今烏里瑪—國家聯盟因石油驅動的“租金主義”而進一步鞏固,如沙烏地阿拉伯、伊朗和阿爾及利亞等國,石油租金不僅強化了烏里瑪—國家聯盟的主導地位,還進一步邊緣化了資產階級。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大約在11世紀,歐洲開始走出黑暗時代。通過政教分離、建立吸引獨立學者的一流大學、鼓勵商人和保護私人財產,歐洲逐漸復蘇——這一切,都曾是此前伊斯蘭文明實現黃金發展的要素。在隨後的500年裡,西歐相繼經歷了文藝復興、印刷革命、宗教改革和地理大發現,這些進程推動了思想繁榮、政治參與、經濟壯大和軍事強盛。而穆斯林世界則沒有經歷類似的轉型,仿似回到了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因此在軍事與政治上逐漸衰落。
西方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項關鍵性的科學發明:火藥、航海羅盤和印刷術。在這三者中,穆斯林軍事帝國只採納了火藥,而對科技發展至關重要的印刷術,卻被穆斯林世界忽視了整整280年。在烏里瑪的影響下,穆斯林軍事統治者視印刷術為危險的技術與潛在威脅。結果,在長達三個世紀的時間裡,穆斯林國家沒有印刷術,造成嚴重負面後果。19世紀初,西歐的平均識字率達到31%,而奧斯曼帝國僅為1%,這也解釋了西方與伊斯蘭文明在識字率上的長期差距。
本書強調,歸根結底,穆斯林國家當下面臨的嚴重社會經濟問題及深層困境,並非源於伊斯蘭信仰本身,也不僅僅是西方殖民遺產或制度缺陷所致,而是王權聯盟長期壟斷權力與思想,再加上石油租金體制的雙重桎梏。庫魯教授提醒我們:只有當獨立的知識階層與新興資產階級重新崛起,穆斯林世界才能擺脫停滯,重建往日的思想活力與經濟創造力。
-------------
編輯:葉哈雅
出處:Dawn News
原文:NON-FICTION: THE DECLINE OF MUSLIMS
連結:https://tinyurl.com/25tl4o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