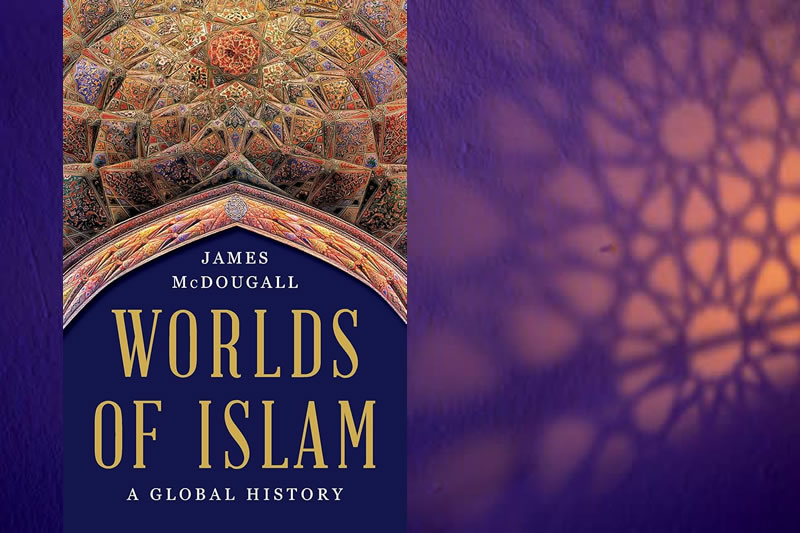西方世界熟知的“地理大發現”,往往被講述為一部純粹的歐洲歷史。然而,若將視角稍作偏移,就會發現:這段歷史從一開始,便深深嵌入了伊斯蘭世界的脈絡之中。
被稱為西班牙“最虔誠的天主教君主”、近代西班牙締造者的斐迪南與伊莎貝拉,他們在15世紀資助哥倫布的首次遠航,並非為了尋找所謂的“新大陸”。他們的真正目標,是從穆斯林手中奪回耶路撒冷,並以此為據點,建立一個面向全球的基督教帝國。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另一位航海者身上。哥倫布遠航的幾年前,15世紀末最重要的歐洲航海家之一,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抵達印度卡利卡特,這次航行常被視為首次打通歐洲與亞洲的直達海路。然而,在這趟航程中,為他引路的嚮導,卻是一位來自古吉拉特的穆斯林。這名嚮導還將他介紹給幾位來自突尼斯的穆斯林商人,這些人會講熱那亞義大利語和卡斯蒂利亞西班牙語,並向達·伽馬祝賀這次“幸運的冒險”。
正是通過重新審視這些看似熟悉卻長期被納入所謂“西方成就”敘事中的歷史細節,著名歷史學家詹姆斯·麥克杜格爾(James McDouga)在其關於伊斯蘭的宏大新作《伊斯蘭的世界:一部全球史》(Worlds of Islam: A Global History)中提出一個核心判斷:伊斯蘭的歷史,本質上是一部具有世界主義特徵的歷史,換言之,也就是一部真正的世界史。
近年來,“全球史”這一概念在學術界和出版界頻繁出現,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被過度使用。許多作品只是將陳舊的帝國史重新包裝,披上“平等、多元、包容”的外衣,以此迎合被稱為“覺醒”的學生群體以及國家資助機構的期待。相比之下,麥克杜格爾這部體量龐大、時間跨度從伊斯蘭起源一直延伸至數字時代的著作,不僅清楚地暴露了上述寫作路徑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他展示了“全球史”這一概念本應如何真正成立。憑藉宏闊的歷史視野和高度具體的敘述方式,《伊斯蘭的世界》回應了哲學家諾曼·布朗(Norman O. Brown)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提出的一項緊迫呼籲:當人們越來越傾向於將伊斯蘭從世界歷史中抽離出來單獨思考時,真正需要的,其實是一部具有世界主義志向的伊斯蘭通史。
麥克杜格爾的跨洲敘述豐富多變,往往出人意料,不僅能拓寬普通讀者的視野,也足以促使研究這一全球第二大宗教的學者重新思考既有認知。作為一名以阿爾及利亞史研究見長的歷史學家,他顯然認真對待了伊斯蘭傳統中“求知,哪怕遠在中國亦當前往”的教誨。循著這一精神,麥克杜格爾追蹤伊斯蘭的歷史足跡,也就是所有自稱為穆斯林的人所生活和活動的地方。麥克杜格爾的敘述從17世紀20年代的卡塔赫納(今哥倫比亞)展開:在那裡,來自不同族群和語言背景的非洲人,因共同的伊斯蘭信仰而形成了緊密的聯繫;接著,他將目光投向菲律賓的一些社群,在這些地方,女性婚前可以擁有多位性伴侶,若婚姻破裂,也可以主動與丈夫離婚。隨後,讀者被帶入南蘇拉威西(今屬印尼),那裡存在著被稱為“比蘇”的第三性別群體,他們在17世紀後從泛靈信仰轉而皈依伊斯蘭;而在西非,麥克杜格爾又指出,幾內亞民主黨政府曾從古代馬里的穆斯林君主那裡汲取政治靈感。
“比蘇”(Bissu)是印尼南蘇拉威西省布吉人(Bugis)社會中被視為超越男女性別的祭司階層,他們通常以“雌雄同體”的身份在伊斯蘭信仰與本土古老泛靈論儀式之間扮演神人溝通的仲介角色。
這些跨度極大、表面上看似雜糅的案例,共同支撐了麥克杜格爾一系列原創卻刻意保持克制的判斷。首先,麥克杜格爾指出,與其從西南亞和北非這些傳統意義上的“核心地帶”來理解伊斯蘭,不如從其邊緣地區,譬如東南亞、西非、西伯利亞、南美和中國來重新審視這一宗教。其次,麥克杜格爾展示了伊斯蘭如何以不同方式抵達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並對當地社會產生深刻影響。換言之,世界上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地區,沒有在某種程度上反過來重塑過伊斯蘭本身。第三,麥克杜格爾認為,西方長期執著於討論伊斯蘭與暴力之間的關係,反而遮蔽了一個重要事實:所謂“穆斯林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往往正是穆斯林自己。最後,他提出一個激進卻清醒的判斷:伊斯蘭究竟如何定義,取決於那些自稱為穆斯林的人如何理解並實踐它,而不完全取決於其是否符合經典意義上的正統教義。
與此同時,麥克杜格爾並未回避提出他對伊斯蘭作為一種歷史力量的獨立理解。在他看來,伊斯蘭同樣可以被視為一種關於權力的政治語言,而這種語言既依賴武力,也同樣依賴論證。將伊斯蘭理解為一種政治語言,意味著必須承認:在歷史實踐中,它能夠容納那些從當代視角看來彼此矛盾、甚至難以並存的傾向。
麥克杜格爾明確否定了當下書寫伊斯蘭歷史的兩種主流腔調。第一種腔調多見於智庫和政策鷹派的論述。在他們眼中,伊斯蘭幾乎完全是一個需要被解決的問題:他們把這一宗教描繪成僵化而刻板,異常強調伊斯蘭教法,並由經文及其正統詮釋者所主宰;第二種腔調,則在“9·11”之後的自由派中流行開來,試圖從最符合多元文化主義和宗教自由價值的實踐中界定“真正的伊斯蘭”。這些出於善意的敘述強調融合性、民間宗教與神秘主義思想,意在說明伊斯蘭的實際實踐往往偏離其理論規範。然而,當面對正統力量在全球範圍內持續佔據主導地位、以及由此產生的暴力現象時,這類敘事往往顯得解釋乏力。
對於上述兩種立場,麥克杜格爾明確表示拒絕接受。他指出,縱觀歷史,關於‘什麼是伊斯蘭、什麼不是伊斯蘭’的爭論從未停止。這種爭論既發生在穆斯林群體內部,也來自外部觀察者。他既不刻意抬高正統、貶低異端,也不偏向理性而排斥神秘;同樣,他拒絕將西方皈依伊斯蘭者視為比生來就是穆斯林的人更“真”或更“假”的信徒。無論是美國的“伊斯蘭民族組織”,還是沙特的瓦哈比派,在書中都被一視同仁地嚴肅對待。那些將菲律賓某王朝的起源追溯到先知與一株竹子的神話,與“伊斯蘭民族組織”堅信白人源于一次失敗的實驗室實驗的觀念,也都被納入同一分析框架。通過這種處理方式,麥克杜格爾反復強調:伊斯蘭,正是穆斯林自我認同與實踐的結果。
這一判斷,在當下具有切實而現實的政治含義。歷史學家和評論者往往在不經意間採納了其研究物件關於“伊斯蘭是什麼或不是什麼”的自我定義。例如,在《大西洋月刊》等媒體上,曾有人斷言“ISIS就是伊斯蘭的,而且非常的伊斯蘭”,卻忽視了伊斯蘭本身長期處於高度爭議之中這一事實。麥克杜格爾明確反對這種教條式結論,他反復強調,激進伊斯蘭組織施加的暴力,更多是指向穆斯林自身,而非外界通常想像中的“異教敵人”。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伊斯蘭國”的聖戰,首先是一場圍繞伊斯蘭正統性的內部戰爭;其次,才是一場自稱代表伊斯蘭、針對非穆斯林的戰爭。“伊斯蘭國”刻意追求全球衝突,並宣稱對發生在歐洲以及美國、加拿大、以色列、莫三比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菲律賓的恐怖襲擊負責。然而,其絕大多數受害者,仍然是生活在穆斯林占多數國家中的穆斯林。
認識到圍繞伊斯蘭的戰爭,往往首先是一場伊斯蘭內部的戰爭,這一事實要求歷史學家具備一種智識上的謙遜。正如那些抵制極端主義傾向的穆斯林常說的那樣:真主最清楚。
這種對研究物件的尊重與謙遜,在麥克杜格爾的書中處處可見。例如,他指出,印尼的第三性別群體“比蘇”雖然自認為是穆斯林,並被視為擁有神秘能力的月亮女神的雌雄同體後裔,但自20世紀60年代起,卻逐漸被貼上“異端”的標籤。麥克杜格爾清楚地展示了,“比蘇”的宗教實踐起源於伊斯蘭傳入東南亞之前。這一例子也正體現了本書所秉持的世界主義史觀:許多被視為“伊斯蘭的”傳統,其實源自伊斯蘭之外的文化土壤。
這種反直覺的洞見,在麥克杜格爾對伊斯蘭起源的重述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這一問題本身極為敏感,對許多穆斯林而言,儘管其信仰與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經典傳統存在關聯,伊斯蘭在西元7世紀的麥加便已完整呈現。伊斯蘭早期信徒以驚人的速度建立起橫跨中國腹地至摩洛哥大西洋沿岸的廣闊統治,在他們看來,這正是真主之意眷顧的明證。
然而,自西元20世紀70年代起,一批歷史學家開始嘗試修正穆斯林關於自身信仰起源的敘述。這些修正往往暗示,穆斯林在歷史記憶上格外輕信,甚至並不可靠,在他們看來,如此迅猛的軍事擴張本身難以解釋,而關於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的諸多敘述,大多形成於其去世一個多世紀之後。無論是丹麥裔著名伊斯蘭史學家派特裡夏·克羅恩 (Patricia Crone)和英國伊斯蘭歷史學家邁克爾·庫克(Michael Cook)把伊斯蘭視為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猶太彌賽亞運動的激進學術論斷,還是古典學者出身、後轉為基督教論戰者的英國大眾歷史學者湯姆·霍蘭德(Tom Holland)對這些觀點的通俗化表達,這類修正主義史觀的共同前提都是:穆斯林史家並不可信,他們借助宗教語言掩蓋政治目的,其統治階層在智識複雜性上也不及他們所統治的基督徒、猶太人和拜火教群體。
與此相對,麥克杜格爾則將伊斯蘭的誕生置於多重交織的政治、經濟與環境危機之中。他既不否認早期伊斯蘭帝國擴張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也不將這一過程解釋為脫離人類歷史的奇跡。他提醒讀者,與先知穆罕默德生平幾乎同時代的基督教文獻,主要為敘利亞文資料,在多個關鍵問題上印證了穆斯林史家的記載。紙草文書和碑銘同樣顯示,伊斯蘭曆法在極短時間內便得到廣泛使用,其普及甚至早於基督教世界以基督誕生為紀年的體系,而後者在歐洲出現已有六百年之久。因此,早期穆斯林關於自身歷史的陳述,其可信度遠高於現代修正主義者通常所承認的程度。
麥克杜格爾的修正並非出於偏見,而是恰恰相反。在重新審視伊斯蘭起源的過程中,他悄然瓦解了“9·11”之後流行的一種看法,即將“聖戰”等概念視為伊斯蘭與生俱來的他者性標誌。事實上,這些概念的思想源頭,恰恰來自伊斯蘭成形之前的基督教政治傳統。聖戰的核心特徵,最早是在伊斯蘭出現前幾十年的拜占庭政治思想中被系統闡述的。
“在拜占庭人看來,波斯的進攻不僅威脅著羅馬的政治遺產,也威脅著基督在世上的帝國。人們首次宣告了一場為捍衛真正信仰而發動的聖戰,並承諾所有在戰鬥中犧牲的人,都將獲得殉道者的冠冕,直接進入天堂。”
通過追溯這些被視為伊斯蘭核心概念的思想譜系,麥克杜格爾的目的在於,去除伊斯蘭被長期加諸的“他者”標籤。
如果這種寫作方式令人感到耳目一新,那是因為它揭示了英語世界關於穆斯林的敘述,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在對“差異”的預設之上,有時是天真的,有時則明顯帶有偏見。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歐洲和北美作者對伊斯蘭的刻板描繪屢屢失准:我們所批評為“東方主義”的那套敘事方式,不僅將伊斯蘭描繪為同質、靜態和本質化的存在,也以同樣的方式塑造了“西方”這一概念本身。
若不重新審視所謂“西方”世俗國家的形成史,就無法真正理解19世紀伊斯蘭世界的政治轉型。通過同時重寫這兩段歷史,麥克杜格爾表明,所謂“穆斯林失敗”的敘事,其實只是一種視覺錯覺。例如,他寫道:
“宗教平等以及世俗國家在宗教領域中的中立性,在歐洲長期並未確立。英國直到1829年才通過天主教解放法案,而在英國統治下的愛爾蘭,教派平等更是遙不可及。19世紀七八十年代,德國圍繞天主教徒的政治忠誠爆發了激烈的‘文化鬥爭’。在法國,政教分離始終是最具爭議的問題,直到1905年才正式立法。俄羅斯高聲宣稱要保護奧斯曼帝國內的基督徒,卻在國內縱容對猶太人的大規模迫害,並將成千上萬的穆斯林強行驅逐出克裡米亞和高加索地區。因此,奧斯曼帝國推動宗教平等,並不是在追趕一個早已開明的歐洲。”
長期主導伊斯蘭書寫的東方主義傳統,無法僅憑一部“更準確”的伊斯蘭史而被糾正。真正需要被重審的,不只是伊斯蘭本身,而是那套用以衡量它的歷史框架——也就是我們習以為常的“西方”敘事。正是在這一參照之下,伊斯蘭被反復對照、反復審判,並被判定為“有所欠缺”。麥克杜格爾所做的,恰恰是動搖這一參照體系本身。正如《伊斯蘭的世界》所清晰展示的那樣,伊斯蘭的歷史並非一段與世界歷史並行的“他者敘事”,而正是世界歷史自身的一部分。理解伊斯蘭,也就意味著重新理解我們所身處的這個世界。
--------------
編輯:葉哈雅
出處:Newstatesman
原文:Islam as the engine of world history
連結:https://tinyurl.com/2c6rl3dh